

小众化农产品的产业化道路还有待多方探索。
云南的一些农产品相继受到资本的眷顾,石斛、玛咖、辣木等都曾显赫一时。风停之后,产业中的虚火泄去,盲目的进入者就进退不得。如何实现一个小门类农产品的产业化,正成为姚安山药面临的问题。
因为色白个大、糯嫩清香等特性,姚安山药供不应求。机遇之下,多家机构参与到其产业化中,并且产学研三界均有;短期看来光明无限,可长远依旧存有种苗、规模上的不确定性。
那么,这股“产业化之风”能吹起来么?
一些人在种植道路上碰壁后,正重新在良种良法、农户合作模式上以及产品深加工上摸索。这是以往没有过的。有人觉得可以学习马铃薯的主食化之路,但也有人认为这有些天方夜谭,不如学习玫瑰的产业化之路更具价值。

市场:鲜货供不应求
和其他山药相比,姚安山药(牛尾巴山药)有着独特的卖点。
海南大学薯蓣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姚安山药的干物质、粗多糖、总蛋白等有效成分含量几乎都高于常见的山药。也就是这样的成分组合,造就了姚安山药色白、个大、糯嫩、清香的特性。“不但是优质菜肴,还具健脾和胃之药用功能。”
姚安人陈春永已经和姚安山药打了10余年交道。在这期间最让他欣慰的莫过于:2014年“姚安山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这是对姚安山药品质最好的认可,同时为产业奠定了基础。”
10余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春永从一个做外贸的朋友处获悉,姚安山药在日本很受欢迎。他就做起了山药收购、粗加工成片以及出口的买卖。做了3年,销售量从600吨上涨至1200吨。
然而,这样的增长没有持续下去。
据陈春永讲述,伴随着当地交通改进,鲜货山药流通速度加快,以及更多农民外出务工,山药种植面积有所减少,再加上姚安山药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在供求上一度呈现出“奇货可居”的架势。
从近期云信记者在昆明市场走访的情况来看,姚安山药在昆明踪迹难寻,零星有发现,而且价格明显高于其他山药。
“从2005年开始,姚安山药鲜货价格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近年来每公斤最高时已经在28元左右了。”陈春永说,“尽管姚安山药片的价格也在上涨,但相距鲜货的涨幅就小巫见大巫了(涨幅不足10%)。”
“面粉贵过面包”的局面,让陈春永改变了自己的商业模式。“在2010年,我便将出口一端彻底关闭,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内销上。除了鲜货而外,还将其制作山药粉进行出售。”姚安山药在研磨成粉后,很容易被氧化变黑,但陈春永表示已经将这个问题解决,并正在申请行业标准。
姚安山药在楚雄除了姚安大面积种植而外,在禄丰罗茨等地也有大面积种植。来自政界的云南山药产业化倡导者李伟,20多年前当农技推广员时就关注姚安山药。
在李伟看来,姚安山药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除了继续出口到日本以及本地的鲜货供应而外,还可以加速研发相关快消品,比如掺入米线等日常食用食品中,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实现姚安山药的规模化和产业化。
事实上,在申请“姚安山药”地理标志商标之初,姚安便寄望于:为进一步发展壮大山药的种植规模,实现质量标准化控制,开展生产加工规范管理,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走品牌发展之路。
尽管和姚安山药打交道已经有10余年,但陈春永自己并没有直接参与到种植环节,在2010年之前主要采取从农民处收购,在量减少后便尝试着与农户合作,承诺“保底价+市场价”(也就是到了收获时:要是市场价高于保底价,就按照市场价来收购;要是市场价低于保底价,就按照保底价来收购)模式来进行回收。

扩种:异地规模化种植成效不大
9月下旬,一场聚集了产学研三界近百人的山药产业行动峰会在姚安举行。云信记者从参会的多位人士处获悉,近年来姚安山药需求不断扩大,价格高涨便是供不应求的直接表现,因为品种独特,像之前文山红甸的山药滞销现象不太可能出现。
云信记者走访了昆明的菜市场,姚安山药几乎见不着身影,甚至有菜贩表示:“要是有人喊着卖‘姚安山药’,那山药一定不是姚安的。”参与到姚安山药产业化行动的吴长立,其主要负责销售方面事宜。他坦言:“目前市场上存有巨大缺口,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既然供不应求,为何不大面积种植呢?浙江商人陈凌云便有这方面的尝试。
2009年,经过多方考察走访,陈凌云发现楚雄当地大多有种植山药的传统,老百姓认知度很高,市场价格也很好,但一直都是农户简单的家庭散种,最大的也只有10亩左右,绝大部分人家仅种三五分地,他当时就有了采用高投入高产出规模化种植的想法。
和其他浙商一样,陈凌云在种植前也非常谨慎。2009年,他跑遍了中国规模化种植山药的大部分县市;2010年,他几乎跑遍了云南有种植姚安山药的地方,采购好的姚安山药种,并收购了一大批食用块茎做成礼盒带到山东、河南、江苏、广西等山药主产区去与当地种植的山药做交换。
“经过比较,姚安山药的品质都得到高度认可,种植户都对姚安山药的品质竖大拇指,我更认定了姚安山药绝对是国内最好的山药。”陈凌云说。
2011年他在禄丰的洪流村租了50亩当地最好的土地,采用每亩4500珠高密植的方法种姚安山药,当年就收获每亩平均2000余公斤的成品山药;按当时每公斤9元的地头收购价,当年平均每亩就能赚12000元,50亩就赚了60万左右,还留下价值近20万元的种苗。
2012年,他将种植规模扩大到200亩,还增加了滴灌设施。“我放下了一个高档海鲜酒店的生意全身心投入管理,为了解决劳力和精细化种植,我特意从省外购买了开沟机,每亩平均又提高了近1000元的投入。当年喜获丰收,平均每亩赚到了15000元左右。此时,我坚信我已经找到种植姚安山药的路子了,剩下的只需要扩大规模就可以翻倍赚到钱。”
2013年,陈凌云继续扩大规模,在禄丰勤丰镇黄陂水库北侧、可里村、高峰乡共租了1400余亩土地种姚安山药。“我是花了大投入的,就连拉网的水泥杆都是特制特配的。”然而,一切并没有如他所预想的那样顺畅。2013年,除去成本,陈凌云不但没赚钱,还赔了800多万,一下就把前两年赚的又赔进去了。
和陈凌云的谨慎一样,经过三四年的追踪,文山添康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立崇决定在文山种植姚安山药,尽管眼下还没有到收获季节,但她坦言:“因为没有控制好水肥等,今年的种植效果并不理想。”前去参加峰会的种植者发出类似声音的并不是少数。
从产业化三要素规模化、标准化和市场化来看,姚安山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规模化的问题,从整个产业行动推进来看,其正在努力攻克的路上。尽管姚安山药已经被引到曲靖、文山等地种植,但是效果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好。陈春永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要是在其他地方能轻易规模化种植,‘姚安山药’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就有些浪得虚名了。”
基于种子的重要,范茂瑄及其团队正致力于种苗的培育工作。据罗茨庄园良种工程的负责人母其辉介绍,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方面是在宣威、富源、沾益等地和玉米进行套种育种,玉米减产不明显,山药栽子增收稳定;另一方面是今年在姚安烟草漂浮育苗大棚的实验成功,固定下原种扩繁模式,初步证明这个利用闲置资源的模式产出的山药品质和一致性更好,还初步判断可以种植两季,且一年四季供应市场鲜山药。

探索:与农户合作屡败屡战
云南的山药市场方兴未艾,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已有大量的人士从炒作“三七”、“石斛”、“玛咖”、“辣木”的阵营逃离;社会对农业的投资冲动却一浪高过一浪,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可姚安山药的产业化,并非就有共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有待解决的问题依然还很多。”云南山药产业化行动项目发起人范茂瑄对此心知肚明。
今年的产业行动峰会已经是第三届,每一届论坛的主题都是指向问题存在之处,甚至可以归结于与农户的合作模式。2014年的主题是:租地雇工干不得。
2014年,范茂瑄及其团队在云南的楚雄、临沧、玉溪、昆明、文山、曲靖搞了28个试验点,并在楚雄禄丰的中兴井以合作社方式搞了千亩种植基地,在曲靖的宣威五里坪搞了一个百亩级的零余子和玉米套种育苗实验合作社,在曲靖的宣威搞了三百余亩传统方式的育苗基地,在曲靖的麒麟区搞了近百亩的家庭农场。
“一年辛苦下来,结果却都是以失败告终了。初看下来,原因很多,可以说种苗不理想,可以说技术不配套,可以说服务不到位,也可以说选人不恰当。”范茂瑄说,“为什么会确定主题为‘租地雇工干不得’呢?因为人们对‘资本下乡’的理解,就是租一大片土地,种上高价格的作物,一年就赚个钵满盆满。即使到今天,这样的念头,依然占据着大多数的有投资农业冲动的人们的头脑。”
“这样的模式也是很多浙商做农业的投资模式,是不具有持续性的。”李伟指出,一旦产品市场低迷,就面临着土地、农民工、肥料等高昂的成本,而无法为继。这在三七向曲靖、红河等地扩种时也暴露了出来。
2015年,继续完善技术配套系的同时,范茂瑄及其团队重点在山药育苗环节突破,先搞三四个和玉米间种培育山药栽子的合作社,引入“行为经济”理念,将农民能做的事交还给农民。此外,这届论坛预见性提出“单打独斗干不好”作为2015年的行动准则。
按照目前的山药种植水平和习惯,以及良种水平,连续三年轮作,山药的产量和质量退化很严重,商品苗的培育也如此。“这之前,我们尝试过用芦竹替换,也尝试过用藤本豆替换,这是两种宿根植物,劳动力依赖小,未来很有前景,却因为我们所选地域大部处于冷凉山区、土地瘠薄,经济价值不高而放弃了。”范茂瑄指出,和食用玫瑰、糯包谷套种会比较理想。
“我们说‘单打独斗干不好’,可不仅仅只是想表达一个常识,是要实实在在做些第三方支持的工作,支撑起一个产业的健康发展,而不是把投资搞成投机,甚至搞成‘赌博’。”范茂瑄说。
事实上,在云南农业领域投资的“赌博”现象近年来层出不穷。其中,玛咖便是个典型。往日通过种植玛咖而赚到钱的云南丽江、会泽等地的农户,到现在都还没有缓过神来,之前媒体相继报道,玛咖的收购价已经从每公斤120元跌落到大白菜价。
2016年的主题是:听话照办有前途。据本报记者获悉,一些种植并没有如预期推进的,大多没有按照相应的要求进行,而是按照传统的种植模式开展。“农民需要的是改善之前的种植思维,是低风险稳健增收,而非‘劣币驱逐良币’带来的伤害。”范茂瑄强调,“听话照办有前途”针对的是农民当前“个体决策和认知能力低下”的问题,在姚安山药产业化推进过程中,要先打通“良种良法下乡最后一公里”的障碍。
这条路本就不是通途。范茂瑄深谙此道:“或许,未来的一年,我们还不能大规模推进商品山药的种植;或许,我们还要花三两年来继续示范推广‘庄园+基地(合作社&家庭农场)’的生产模式;或许,我们还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逾越‘龙头企业+农户’形成的障碍。”

产业化:“必须走向主食化”
姚安山药要产业化,主食化势在必行——这是各方面人士的共同观点。
谈及主食化,近来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马铃薯成为我们第四大主粮”。眼下,用马铃薯加工成适合中国人消费习惯的馒头、面条、米粉等主食产品,实现马铃薯由副食消费向主食消费转变、由原料产品向产业化系列制成品转变、由温饱消费向营养健康消费转变,作为我国三大主粮的补充,逐渐成为第四大主粮作物。
类似的行动,在姚安山药一端也正在推进。
“除了鲜货、切片、粉末而外,我们也正在尝试着更高附加值的制品,比如山药米线、山药饵块等。”据陈凌云介绍,目前正在北京筹划着开提供这样食材的连锁餐厅。与此同时,与山药相关的更多产品也正在研发中。
山药,算是功能农业产品的范畴。“说得简单点,功能农业就是指农产品的营养化、功能化。体现着东方人、中华民族‘食药同源’的智慧,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方向。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其一是高产农业,其二是功能农业,优胜之道是二者结合。”同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敬华指出,“并不是有资源优势的功能农业就一定有好效益。‘富硒’粮菜产区并未形成优势产业,‘茶叶籽油’是养生极品也符合国家粮油政策还是没造福一方。”
在杨敬华看来,姚安山药要实现产业化,有四道坎是必须逾越的:
品种。任何一个品种长期没有经过科研提纯复壮,必将会遇到病毒,面临着退化的。任何一个产业的开始得从种子开始,培育良种是首要的。面对着姚安山药这样的小品种,保持着种苗的优良性,科研必须跟上。
土壤。之前大多姚安山药都是纵向种植,但并不是所有土壤都能满足这样的条件,所以经过改良后弄成了横向浅层种植,经过改变作物种植方式,可栽培的面积扩大。同时,在扩种过程中,不是所有的土壤都能够培育出优良产品,如何通过改良突然,让扩种、规模化得以实现,也是必须逾越的。
组织。目前姚安山药的种植模式,要是不经过组织,也就是小农经济,从目前看来小农经济并不适合市场化发展的空间,必须得把农户组织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就面临着组织模式的创新。
市场。一家一户的农户不太可能去打市场,在给农民打市场的过程中,农民的契约文化意识薄弱,往往逐利而动,行情好的时候,就和你无关,而行情不好的时候,便会主动与你走近,如何扭转这样的态势,也是必须逾越的。
在小众化农产品产业化过程中,资本往往是始作俑者。以玛咖为例,原产于南美高原的玛咖,14年前在云南丽江培植成功。由此,诞生了玛咖这一新兴产业。云南省政府也曾在境内组织农户种植,面积越来越大。
玛咖也成为资本市场热炒的对象。早在2011年,就有上市公司布局,试图做大做强,可如今受供需失衡等市场因素影响,未能形成庞大产业链。事实上,玛咖并不像三七、石斛那么被人们所了解,因此夸大宣传、种植混乱等问题,接踵而至。
“炒作,都是带有泡沫,价格严重偏离价值,当价格不足以支撑价格时,泡沫也将被刺破。”杨敬华指出,“玛咖、石斛不具有一种必须性,而姚安山药要把产业化推向主食化,未来还可以赋予抗氧化、抗衰老等功能。”
这方面,“玫瑰的产业化之路”便是典范。

产业化六环节缺一不可
“后来搞农业经济的专家告诉我,有六个环节,你只要每个环节打点折,哪怕是九折,叠加下来,成效已经大半不在了。”陈凌云将自己亏损的原因归结于六个方面:
第一、土地问题。传统种植方式需要几个条件:可以深耕1米2的土地,沙化要理想,水源要有保障,土地肥力要足够,这样的土地在云南十分稀少,陈凌云租下来的这批地质量打了折扣。
第二、劳动力问题。购买来的开沟机不能在砂石多的地块上发挥作用,只能采用人工方式来完成,结果花费了巨大的资金,还耽误了农时。
第三、种源问题。规模扩大后需要大量的种子,市面上无法买到足够的优良种子,散收来的栽子出现了大量的缺苗、弱苗、死苗。
第四、田间管理问题。规模化后管理的成本加大了,特别是除草费时费工不说,雇工困难造成了除草不及时。
第五、病虫害问题。罗次坝子的土地通常冬春季不休,导致病害虫害严重,而山药是食用块茎,不能过度用药,这下麻烦可大了,三分之一受了灾。
第六、采挖问题。和上两次的地块不同,黄坡水库的地块到了干季坚硬得很,费工不说,挖伤挖断的实在太多了,这可就不值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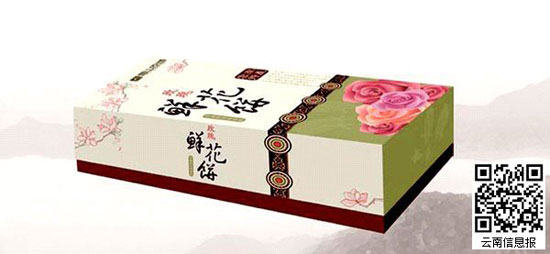
他山之石
玫瑰的产业之路
而今,玫瑰鲜花饼几乎成为来云南旅游者必带的伴手商品。“以前来云南旅行的除了普洱茶,带的是鲜花,现在改成了鲜花饼。”有着“玫瑰花王”称谓的朱应雄说,“姚安山药的产业化必须要如此,来云南旅行也将其当作伴手礼,才可以说是成功。”
伴随着大健康概念的提出,姚安山药的机会和当年玫瑰花一样,也出现了商机。“但机会只有3年。”朱应雄说,虽然山药是个小品类,但在大健康产业中可以扮演着重要角色,只能从功能的角度来进行突破。
“以云南鲜花为例,经历了之前的鲜切花时代,而今在兼具观赏功能的同时,也走向了食用方面。风生水起的食用玫瑰,是花卉升级版,跨越式发展。”朱应雄谈及玫瑰花产业化过程时,指出其三要素:规模化、标准化和市场化,这三者是个层层推进的关系,没有规模化就没有标准化,没有标准化也就没有市场化。对应的是市场链接、标准规范和农户组织都要做实,缺一不可。其中,农户组织是最为头疼的。
下海前,朱应雄是通海县种子公司的经理。当时,很多花卉种植公司一直沿用着“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即公司将种植外包给花农,待花卉成熟后,以协议价格收购成品花,最后在花卉市场按照市场价出售)。这种模式的弊病是,如果花的市场价低于买断价格,农民会把不是基地里面的花也送过来;如果花的市场价较高,农民也总会有办法把基地的花偷送到外面去卖。
注意到这样的情况,朱应雄建设性地开创了一种产业模式:“品牌+农户+市场。”在处理公司与农户的利益关系问题上,朱应雄进行了一番设计。他表示,“农民在产业链上做他应该做的事,种出来的花交到我们公司,但花还是农民自己的花,就按统一标准给花做加工,每枝花我们提相应的服务费用,包括包装纸、运输费、加工人员的工资等。虽然这些花都标上了我们的品牌,但多卖的钱都归农民所有。”
在玫瑰花全产业链的过程中,朱应雄是从源头的种子开始,目前他的玫瑰资源库就有3000余个品种,从而保持了品种的优良性。而今,朱应雄玫瑰花的种苗供应、庄园建设、产品导向体系已经形成,并已经进入提升阶段,目标指向三个方向:“成为功能食品:功能+情调+主食化应用;成为标准化商品:可评价、可计量、可追溯;成为社群快消品:社群细分、新生代加入。”同时他的市场格局已经形成了:立足云南,在北京着眼于文化高地,在深圳对接市场前沿。
对于正在推进产业化的姚安山药,朱应雄坦言:目前就没有做到产业化三要素,要加快其产业化路径:缺优质种苗是瓶颈,必须产学研结合助推“原种快繁+融资”产业提速;逐步建立对种子分级标准管理和商业定价系统,实现在种苗上的优胜略汰;在种植过程中,采用和玉米等作物的伴生模式,以降低农户种植风险。(云南信息报 记者黄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