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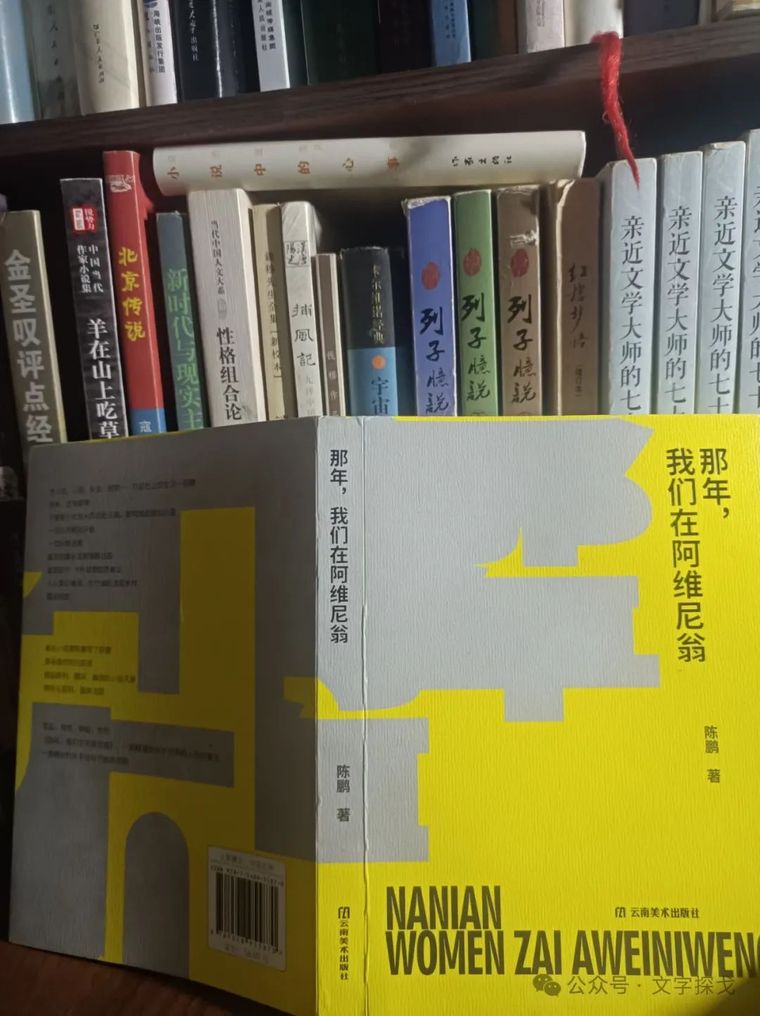
爱情的理想文本演绎——陈鹏小长篇《那年,我们在阿维尼翁》阿探在长篇小说《群马》(《收获》2023 长篇秋卷)里,陈鹏展示了超乎常人的叙事长句,并使之成为文本精神叙事气质的一种独属。而在小长篇《那年,我们在阿维尼翁》(《江南》2022年第6期)中,他又以力量感超强的短句,让读者重温了海明威式的极简主义。阅读前者,是沉闷重压心灵的艰辛之旅;精读后者,无论从前往后读,还是从后往前读,都是精神愉悦的,因为我们至少在某一刻都是小说中的人物,甚至主人公最终的爱情境遇亦即人类无以挥去的命运注定。
在笔者看来,《那年,我们在阿维尼翁》并非爱情小说。爱情只是陈鹏文学雄心籍以附着性构架,尽管小说尽述杜上、米苏之爱情逃离中国式种种束缚,奔袭法国南部及至最终的消失,但笔者依旧坚定地认为,那只是陈鹏小说观神魂的演绎过程而已。陈鹏之于中国文学,绝对是异类式的存在:在早年先锋文学代表们最终选择了妥协、投降于文学现实生态多年之后的今天,他依旧奉先锋文学为圭臬,以个体之突围与几近沦落的中国文本常态作战,为中国文学占据世界文学经典一席之地做着无惧无畏的努力,颇有些“一个人的运动”之决绝,亦即小说主人公杜上式决绝。换句话说,《那年,我们在阿维尼翁》在本质层面是陈鹏在以小说的方式表述他的理想文本的内质构建过程,毋宁说陈鹏在竭力构建一场决绝的纯粹爱情,不如说他是以构建的方式摧毁了这场深入心魂的爱情。他选择了让杜上与米苏颠覆伦理常态式“伟大”爱情的沦陷与消解殆尽,由此让文本探究了爱情更加层深的未知未至领域。小说在爱情狭隘意义消散之上,以理想之文本构成,扩展了人们未曾认知的爱情领域。事实上,他近几年了发表的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他小说观的文本性宣示,为了强化这种宣示的表达,他甚至以作家“陈鹏”屡屡走进文本。在这个意义上,近两年来陈鹏的大多数文本都富含着元小说的意蕴。如果说他以前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的小说观宣示意义不够明确的话,到了《那年,我们在阿维尼翁》,几乎已经是完整的系统化表达了。
《那年,我们在阿维尼翁》的叙事貌似黄河穿越晋陕大峡谷,跌宕起伏,拥有着强势而静美的雄壮;又似陈鹏本人在绿茵场上的躲闪腾挪、长驰突进之雄姿风威;整体上亦不失高山流水之自然韵美。沉力潜心的内质性架构,可击溃中国大多数长篇解构,甚至包括很多大奖文本。尽管陈鹏崇尚西方文学经典,笔者依旧喜欢以中国经典文学认知去阐述这部小说的奥理所在,因为正如小说《后记》所道“中外作家观点确有差别,但文学无国界”,依旧可以“平等自由的对话”并达成“共识”。笔者始终认为,陈鹏超强的小说结构意识,对普遍丧失了结构意识的中国长篇无疑是一种强力提振与重要启示。小说叙事有疾有缓,无异于一部经典的爱情电影。
《那年,我们在阿维尼翁》的结构,是超越了常态惯性与乏力的富于现代性张力与弹性的复式精微。小说由两个三重架构,两个三角恋建构而成。文本贯通性三重架构由书外的著者陈鹏(开篇的文本缘起自述者)策动与主导,以主人公杜上纯然纯粹性爱情的奔突,最终到小说人物作家“陈鹏”以无迹无形的文学之力最终让杜上的爱情沦陷至消失的过程,这是一个升华的过程,是从现实认知及其种种束缚中至文学无限广义之境的迈进及腾升。小说在核心内容上由现实层面超乎常态的爱情奔突与爱情沉淀及升华的法国南部阿维尼翁地区的历史性文学疑案的探究构成,后者则是跨国别的内在支撑性三重构架:由入法籍住在蒂日涅小镇的一幢大宅里脱离了爱情束缚的秦姐为中心,关联起来美国女人克里斯蒂娜与法国男人蒂诺的老少恋,法国艺术家米歇米,与另一个艺术家皮埃尔及其妻子玛丽琳之间扑朔迷离的多角情感交错,1999年夏夜在鳄鱼村上演的戏剧《那年,我们在阿维尼翁》。两个三角恋则是主人公杜上、米苏及文中作家陈鹏及戏剧《那年,我们在阿维尼翁》中三角恋。两个三重构架与两个三角恋,外加历史过往中克里斯蒂娜与蒂诺,米歇米,皮埃尔及其妻子玛丽琳之间超乎爱情束缚的多角情感关系互为镜鉴,彼此映照,合力共进,最终彻底消解了杜上与米苏之间老少恋。
虽然杜上年近五十,尽管他有着于一切决裂的大勇,却并不明白爱情对于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甚至是在19岁的米苏的导引下,才有了远赴阿维尼翁之远行。秦姐对于杜上而言,是全然理性的镜鉴者,她早年就明白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所以弃绝了爱情干扰来到法国,她最终如同林黛玉引领贾宝玉的精神一样导引了杜上:“我挺你。总要往前走啊,总要把黑洞堵上,总要从坑里爬出来。拼命爬出来。”而文中作家陈鹏,则从精神层面促进了杜上彻底性地脱离爱之泥淖,他最终明白了爱情意味了对无限可能的包容。热恋中的米苏提到阿维尼翁绝非偶然,她读过很多文学作品,对文学艺术有着过人的精准认知,阿维尼翁是她期望的并不明确的精神超脱之地。作为一个有无限可塑性年轻女子,遇到文中作家陈鹏,她的精神又一次被重塑,清晰了自己原本并不明确的寻找,她被陈鹏所导引而进入了超越与杜上老少之恋的更广阔的精神之境。于是,杜上与米苏的爱情奔袭,远赴法国,成为一场爱情求解与沉淀的魂动之旅,克里斯蒂娜与蒂诺、米歇米、皮埃尔、玛丽琳之间关系骤变之谜以及在鳄鱼村上演戏剧《那年,我们在阿维尼翁》,则是他们认知爱情更广阔更幽深内涵的精神密钥。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杜上与米苏,在先锋文学意义上则是中国式精神模式制约的颠覆者,他们的爱情逃离与奔袭,抵达了了文学(文本)更多元更无限的内涵与境地,这正是著者陈鹏爱情小说宏阔之境的天成:以竭力构建完成对初始构建的颠覆与摧毁,在摧毁中孕育爱情无限之可能的绵延。
读完小说,站在文本之上俯瞰,会有更清晰的认知:70后杜上的爱情经由的自然的缘起,公司中与90后的暴力冲突,并由此而决绝地洞穿公司各层面的种种障碍,越过米苏父亲老周的传统伦理观念的鸿沟,来到充满了迷离、不确定性的法国南部小城尼姆,最终在鳄鱼村悄无声息地消失,而主人公杜上却迎来的是精神的释然。或许对于从三角恋中骤然退场的米苏与文中作家陈鹏而言,也是一种释然,如同克里斯蒂娜与蒂诺、米歇米、皮埃尔、玛丽琳之间友谊的骤然终结。著者陈鹏作为中国绝好的小说家,他将自己精神裂像为现实中有些精神自囚的杜上,文学无疆之域驰骋的文中作家陈鹏,在三人基于有关阿维尼翁文学幽深本质性精神思辨及共振中,以爱情为名义演绎出了几近理想态的长篇文本。虽然不论是杜上还是米苏,虽然他们并未真正抵达阿维尼翁,亦即他们的爱情决绝未能抵达理想之境,阿维尼翁最终成为爱情爱情的冰释、消散殆尽之地。
小说不仅有着极简有力的富于精神承载的金句,更有了各个层次人物所构筑整体性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的精神幽深对主人公的精神陪衬,亦有细腻有致的恋爱进行时现场与彼此过往的深入追溯,有对爱情多变脆弱的超理性的概括,有对情感秘密黑洞的永不揭示,更有爱情未知未至领域的积极探索,比如克里斯蒂娜与蒂诺、米歇米、皮埃尔、玛丽琳之间友谊的骤然完结的种种可能推测。从爱情被不同层次、系统(公司中代际之嫉恨、部下之私心、高层之要面子;老周的传统伦理观念之不容等)的束缚、挤压、重压,到法国阿维尼翁鳄鱼村宁静中过往幽深的情感激荡及永远的沉寂,著者陈鹏直面人之精神质地,捕捉了爱情的纯美并以终极性开掘定格了其纯美的脆弱、易碎。
小说叙事从容、克制,密伏处处,前后相互映照,互文互解。比如,前半部分“消失”是个多次出现的词汇,有对突然消失所造成的单方精神恐惧的有意为之,后文最终米苏的消失犹如杜上前妻刘盐的消失;再如,前文有对“秘密”阐释与强调,后文有克里斯蒂娜与蒂诺、米歇米、皮埃尔、玛丽琳五人友谊骤然终结的多种可能之探索;比如,前文有对契约型夫妻关系脆弱的思辨,情感的罪感,宽宥,精神刹那间的恍惚等,后文最终有米苏悄然地消失及杜上最终的心灵释然;前后文更有着丰富的音乐、电影、诗歌等多种艺术交汇的独有的相互性精神印证;有对过去的持续性决绝,亦有对理想之境的长久渴望,更有爱情自然永逝的如释重负等等。而这一切所有之中,最重要的则是文中作家陈鹏的文学性阐释与引导,以及秦姐的人生本质性引导。
这场质地相当的爱情经由世俗安身立命的决绝放下、逃离、奔袭赴远的爱情,如同人世一场大宴狂欢,最终只留下一丁点清凉慰藉,即便杜上与米苏赋予它以决绝的俗世代价,然而人间短暂鱼水之欢亦无法抵御最终离散。罗伯-格里耶认为,“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对于著者陈鹏而言,所幸还有他所认定的理想的小说文本可以定格爱情这悲壮的诗意。(本文作者:阿探)

《那年,我们在阿维尼翁》作者陈鹏
陈鹏,1975年生于昆明,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云南作协副主席,昆明作协主席,小说家,曾获十月文学奖、湄公河国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出版有中篇小说选《绝杀》《去年冬天》《向死之先》,长篇小说《刀》《那年,我们在阿维尼翁》《群马》,足球短篇集《谁不热爱保罗·斯克尔斯》等。